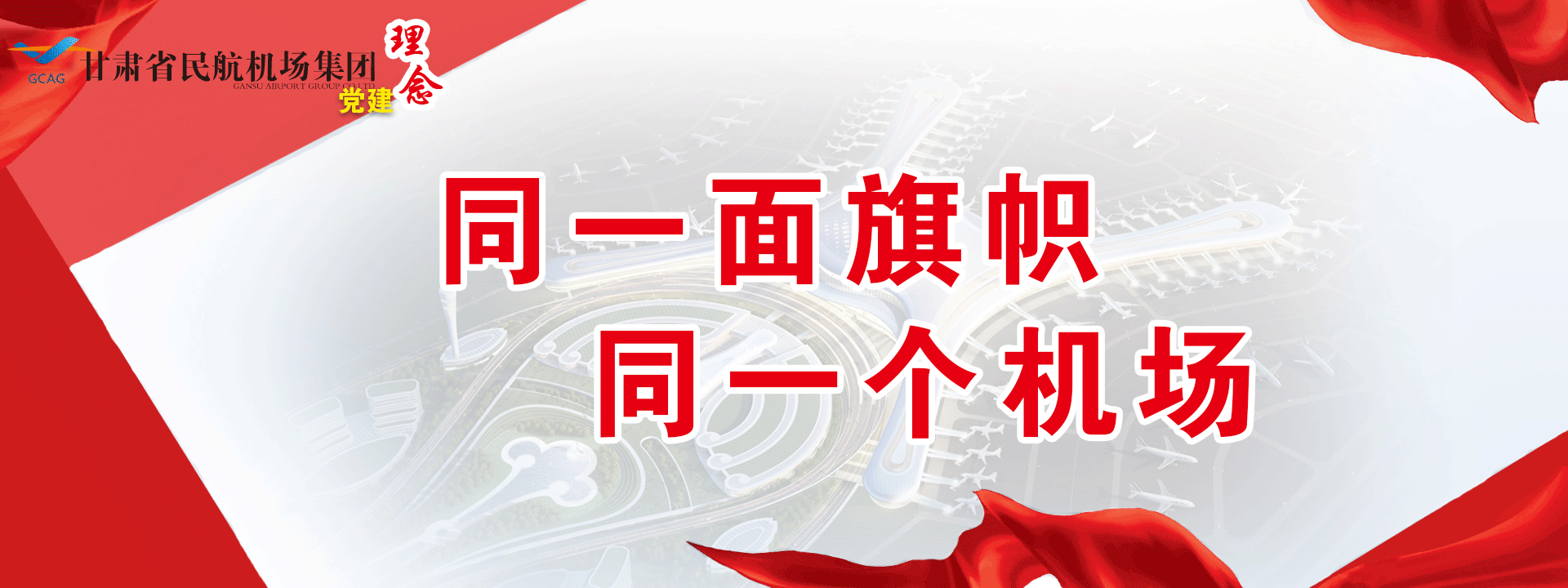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定义较为宽泛,诸如收藏文物的民众教育馆、举办展览的科学教育馆以至水族馆等均被学界视为博物馆。甘肃是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甘肃省教育馆更名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中英庚款理事会设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各县战时陆续创设民众教育馆并举办陈列展览,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在大后方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精神助力,播下了科学之火。

武威文庙旧影,当年曾辟为县民众教育馆。甘肃省图书馆藏
民众教育馆前身系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5年通令各省设立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之通俗教育馆。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改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1926年,时任甘肃省省长薛笃弼创立甘肃省教育馆,直隶省政府,省政府秘书长兼任馆长;馆址设在兰州西大街庄严寺内(今张掖路大众巷内);次年附设国民音乐研究会。该馆内设图书、讲演、博物、游艺四部,其中博物部分史地室、理科室、美术室、卫生室、教育室,游艺部分运动场、游艺室、电影场。
“九一八”事变后,依照国民政府1932年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水梓呈准省政府将甘肃省教育馆改隶省教育厅,更名为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委张懋东为馆长,内设陈列部、讲演部、游艺部、生计部、健康部等,将兰州庄严寺大殿及前后院厢房40余间,分别改建为图书、讲演、博物、游艺4个部分,计有书画研究室3间,展览陈列室13间,办公室6间、游艺室3间,另附设民众礼堂、民众食堂、民众茶园、体育场等设施。该馆工作人员包括馆长1人、主任干事7人、干事2人、管理员3人、司事1人,职员薪俸最高额80元,最低额16元。该馆每年“由省库支领经费6000元,尽数作为职员薪俸及设备购置等费”。其中陈列部“搜罗各类古物暨文艺等件,陈列室中,供游人之展览”。据1936年统计,该馆收藏古物138种、书籍918部、各种博物41种、各种字画碑帖59种、各种照片邮票949张、各种器具552件、电影配乐13种。

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标本陈列室。
全面抗战爆发后,官方和文化机构都重视以展览形式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郭沫若指出:“如战利品展览、防空展览等,凡是搜集同类宣传资料供公众阅览的方式都是展览。”博物馆学家陈端志亦强调:“展览宣传为民众训练工作中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方法”“就是任何人的心理,也是喜欢看一处展览会,比听一次演讲的兴趣来得高”。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配合抗日宣传和国防教育需要,亦曾举办过日机残骸展,展出兰州空战中被击落日本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部分遗物,观众数万人次;此外还举办过空军史话展。据叶建军《回忆八年抗战期间的兰州防空》一文载,1939年2月27日至3月2日,在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的敌机残骸展览会上,陈列敌机机身、飞机零件、机枪、军旗、地图、佩刀、护身符、佛像等,作者参观展览时观察记录甚细,指出敌机残骸系侵华日军装备的意大利造轰炸机,装备12.7毫米航空机枪1挺、7.7毫米航空机枪3挺,所配弹链每隔三五发便有一发为指示弹道的曳光弹(弹尖红色),其中1把日军军刀刀铭为“明治二年三月义明夫人广房作”,算起来也是有70年历史的家传之物,最后成了中国军民的战利品。

兰州庄严寺天王殿内的塑像,该寺当年为省立民众教育馆。甘肃省图书馆藏
除了省立民众教育馆外,早在1919年,张掖县即成立通俗教育馆;20世纪20年代,静宁、酒泉、崇信、渭源、礼县相继成立通俗教育馆。“九一八”事变后,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地处西北的甘肃亦有“唇亡齿寒”之感;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颁布《甘肃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县立民众教育馆须设阅览、讲演、健康、生计、游艺、陈列、教学、出版、事务等九部,以唤醒民众、启迪民智,其中陈列部职掌为“标本模型古物书画照片图表雕刻工艺各种产物博物馆及革命纪念馆等属之”,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了县级民众教育馆兼具博物馆之职能。如1934年成立的武威县民众教育馆,以文庙文昌宫为馆址,以收藏展览地方历史文物为主要职能;1938年改文昌宫西楼为图书楼收藏古籍,东西两廊房间辟为展览室,诸如西夏碑、弘化公主墓志等著名石刻文物均系这一时期入藏。
全面抗战爆发后,甘肃相关县陆续设立民众教育馆,兹按时间顺序分述如下:1937年,岷县民众教育馆在民间募集古代刀剑、弓箭、盔甲、鎏金佛、古陶器等,在馆内举办展览。1938年,靖远县设民众教育馆,收集和展览地方文献、古物、军械、金石印章、先贤事略和遗像、地方工艺样品、龟蛇石碑。1940年,西和县民众教育馆迁址城隍庙,将该庙部分房屋改建为阅览室、游艺室、文物陈列室。1941年,徽县在南街药王庙设民众教育馆,设有阅览室、陈列室、办公室及舞台1座,有图书杂志300余册,陈列县内土特产、出土文物、名人书画等,每天开放8时。 1943年,西固县(今舟曲县)在文庙设民众教育馆,展览甲盔、军械等文物;同年,武山县设民众教育馆,馆址初设县城前街,后迁后街天爷庙,有图书与陈列二室,图书室有少量古典书籍,供读者阅览,陈列室展出古陶器物、龟甲等;同年成立的和政县民众教育馆,有工作人员3名,县政府每年拨法币1100元作为经费,订有报刊9种,藏书百余册,并陈列数件古代盔甲和出土陶器、铜器。
据《抗战期间之甘肃教育》一书记载,地方当局对于战时各级民众教育馆建设运行给予一定支持,“复以天水平凉武威三县民众教育馆,地位重要,先后改归省立,增加经费,充实内容,俾为附近各县民教馆之模范”,同时将县级民众教育馆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安排财政预算;然而,“抗战以还,本省社会教育虽经计划推行,但以物力不足,人才缺乏,未能一一适如所期”,这也导致抗战时期成立的部分民众教育馆时有存废,但相关民教馆的文物藏品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文化馆或博物馆的物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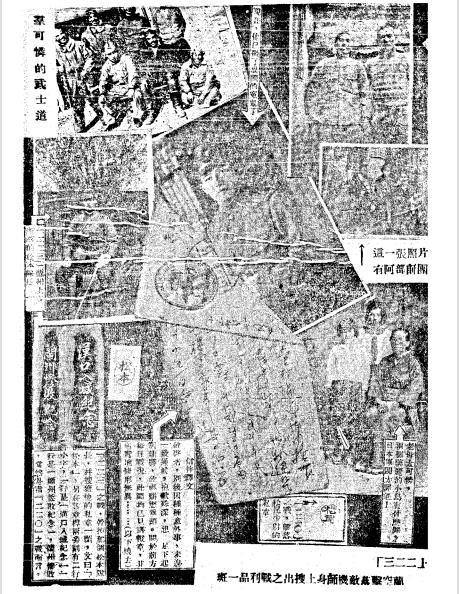
1939年2月在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展出的被击落日机残骸中发现的战利品。引自《中国的空军》1939年第22期
说到抗战时期的甘肃博物馆事业,甘肃科学教育馆(1944年更名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该馆承担了战时部分教育行政职能,如面向中小学校制造赠送科学教育器材,为兰州市各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课程提供场所和设备,受权承担师资培训、试卷评阅、巡回指导等工作;发挥自身优势,为省内相关机构提供矿石标本化验、检测等服务,调查兰州市水质和蓬灰资源……堪称“全能型选手”。从博物馆角度考察,该馆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惠泽后人。
一方面,该馆广泛收集整理自然标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博物馆相关馆藏基础。该馆成立后,与省内外相关高校和专科学校合作,在兰州周边、河西走廊、陇东南地区开展生物资源调查工作,为日后编写教材和筹办陈列展览积累标本资源,仅1939年年内就获得动物标本五千余件、植物标本万余件。1939年至1942年期间,甘肃科学教育馆馆藏昆虫标本共20目135科1326种8164号,其中蝶类标本150余种,在此基础上,该馆抗战时期陆续出版了《甘肃蝶类初步报告》《甘肃蜻蛉类初步报告》《兰州植物志》等成果。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举办陈列展览培育民众科学精神。受抗战期间客观因素制约,甘肃科学教育馆成立后一直租用民房或借用校舍,抗战末期才争取到固定馆址,至1946年方开辟60平方米的小型展厅,陈列展示馆藏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尽管该馆已经认识到“各国大都市均有博物馆之设立,意在启迪民众科学智识,并供学校师生观摩阅览。本馆设备有限,历史浅短,欲求企及博物馆之规模,势不可能。但小规模科学陈列室之设置,实不容缓”。然而受馆舍条件限制,其陈列展览可以用“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借船出海”形容,如该馆在1941年度“曾就图书室、会客室、膳厅、中心实验室等处,略予布置,陈列一部分挂图、仪器、标本之类,以供众览”;同年10月,该馆将理化仪器、生物标本、科学模型以及挂图表格等件,借用省立民众教育馆馆舍举办科学展览会,历时三日,每日由馆派员指导,观众络绎不绝。“惟前者范围过小,不成体系;后者为期太促,收效难宏。”李烛尘《西北历程》一书曾记录了其于1942年10月27日参观甘肃科学教育馆的情景:“承馆长袁翰青先生招待指示,得历观其动植矿之标本室,均藏甘省产品,真是琳琅满目。在边城交通不便之地搜存如此之富,可见工作人员之费心力不少。内有多数沙漠植物,为全国各地所绝不能见到者。”
以今日博物馆学视角考察,抗战时期的甘肃各级民众教育馆承担和发挥了历史博物馆的部分职能、甘肃科学教育馆承担和发挥了自然博物馆与科学博物馆的部分职能,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了抗战烽火中的陇原博物馆事业。相关史料对于甘肃抗战史、博物馆史具有重要意义,有待深入挖掘和进一步研究。
文丨史勇
来源:奔流新闻

| |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