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的时候,爸爸出门,我必跟去。那辆饱经风霜的“二八”式加重自行车,比我大好多岁,车子上紫红色的大梁被磨得锃亮,那是我的专属宝座。爸爸骑着它买粮、驮煤,串亲戚,我斜坐在大梁上,小小的身躯趴在车把上。爸爸温暖的鼻息均匀地吹在我的头顶,眼前的景物风驰电掣般甩在身后。父女俩有一搭无一搭地对话,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爸爸高兴地带我逛一个个商铺。那时,整个太原的铺子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坞城路副食店离家最近,掀开厚厚的布帘子,浓浓的酱油醋味扑面而来。爸爸最爱看瓷器,为了补齐不小心打碎的碗碟,会在里面精心地挑选。东太堡商店那时看来在东山的方向,要经过铁道。长长的栏杆徐徐落下,行人被呼啸的列车挡在两旁,巨大的木牌上写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再往北走渐渐繁华,大营盘、并西商场、五一大楼等。其中,五一大楼几十年里一直是太原城的标志性建筑,小时候觉得宏伟极了,里面更是琳琅满目。在我看来无比新奇的是收钱方式。售货员开好单子,和顾客的钱夹在一起,顺着头顶上方的细铁丝,朝收银台方向“嗖”的一声划过去。不一会儿,夹子“嗖”的一声又飞回来,夹着找回的零钱和发票。顾客熙熙攘攘,头顶铁丝密布,黑夹子像小火箭一样排队发射,满天飞舞。
在那个拮据的年代,爸爸为了买到更结实耐用又物美价廉的日用品,骑着自行车不辞辛苦地在城里穿梭,挑了又挑,比了又比。我也跟着他时常光顾这些今天看来选择其实少得可怜的店铺。一个冬天的黄昏,路过一家店,爸爸突然想起有样东西要买,为了省时间就把车停在路边,嘱咐我看着:“如果有人要推走,你就喊这是我家的自行车!”还没上学的我点了点头。爸爸的身影在夜幕中闪进商店。我伸出小手攥紧后座,心里忐忑不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时刻准备喊出那句响亮的口号:“这是我家的自行车!”爸爸终于出来了,无惊无险。
有一次,遇到一位老爷爷,身板结实,笑声爽朗,和爸爸并肩骑着。爸爸说:“爷爷是老红军,战斗英雄。”我这才注意到,爷爷左腿裤管是空的,一支拐杖放在手把上,右脚从容地蹬着车子。年幼的我,顿时肃然起敬。
上五年级的时候,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爸爸带我走亲戚,路上商铺还关着门,红红的对联透着喜庆。我不住地念,发现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难道不应该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吗?”我不解地问。爸爸说:“对呀,我也这么觉得。”那时,我们都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上,金钱这个不甚被人们接受的字眼,突然之间铺天盖地地登上大雅之堂。之后,全国开始轰轰烈烈地改革、下海,金钱致富也就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上中学前,爸爸为我精心挑选了一辆崭新的太原产“铁锚”牌黑色女车,从此整个中学时代我就自己骑车上学了。再次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已是13年后。那是1998年出国前夕,爸爸专门请了假陪我采购生活用品,带我去新开的美特好超市。我坐在后座上,爸爸依旧骑得稳健有力。光阴荏苒,转眼我在美国也20年了。自行车早已不再是交通工具。父母来时我开车带着他们,父女俩依旧聊天说笑。儿子小时候曾天真地问:“姥爷,汽车为什么有灯呢?”爸爸答道:“汽车的灯就相当于人的眼睛呀”……祖孙俩的对话,瞬时又勾起我童年在自行车上的回忆。
如今的家乡变化日新月异,到处是商店。爸爸甚至学会了淘宝网购。并州路、长风街,架起了高速立交桥。爸爸偶尔还会骑车出去转转。当年带着我的时候,爸爸是个青春小伙,蹬着自行车,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晃岁月流转,时空巨变,而爸爸对生活的热情,对女儿的关爱从来不曾改变过。自行车印出的道道年轮,伴着大梁上那个扎羊角辫小姑娘银铃般的笑声,从70年代那一端,一路流淌至今。
魏婕(美国)
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李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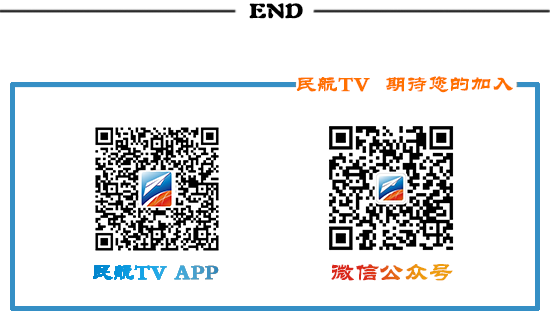
我要评论